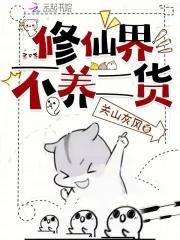書趣閣>亦醒亦醉 > 第123頁(第1頁)
第123頁(第1頁)
四清自你少時便一手教輔,無論國事再忙,對你的課業也總是親自過問,可謂嘔心瀝血。身為人臣,四清與我共定益州,年少出使雄辯、屢入險境;而今四清雖大權總攬卻毫無不臣之心,依舊兢兢業業。可你倒好,一句‘司文司武互不相幹’将你的老師、将我定國重臣、将我引頸之交氣得栽倒在路上。
劉緻啊劉緻。你在殿上數次無禮,頂撞于我和四清,空談太仁。四清均勸我‘少主年輕氣盛,過些時日必成大器’。今日你鑄成大錯,我扪心自問一番,我是太過于仁厚,當你第一次現出狂浪姿态之時,我便應當狠做敲打,若當初如此,興許還能力挽狂瀾……”
劉項有些發愣地望着地上跪着的劉緻,心中不解究竟是何處出了差錯,怎麼他的兒子陡然長成了這幅模樣,陌生的,他像是從來不識。劉主公深歎口氣,說:“你現在,對着先祖靈位反躬自省,仔細思量你的錯處。”
殿内的長明燈燭将劉圖南鍍上了一層暖金,他身上淩亂地挂着主公冕服,額上還留着方才束帶滾邊留下的擦痕。
他深伏一禮,望着列祖列宗靈位,開口說:“四清老師之事,原是我不對。此事過後,我自會去老師府上負荊請罪。
至于戰亂之苦,眼下隻是空有一統,現在同公父所經曆過的大争之世有何區别?吳國吞豫,冀州伐戎,涼州騷亂紛紛,就連荊州也不住躁動。這世道早就亂了,隻是公父不肯睜開眼看看罷了。”
劉善德繞到劉圖南正面,仔仔細細打量了他一番,好似全然不識這是自己的兒子。
劉圖南接着說:“此番蜀商滲透口岸,挾持荊州辎重;常歌詐使夷陵分兵攻九畹溪、趁機奪了夷陵;建平内外夾攻,太守都尉一舉殲滅;荊州北部着實給我們吃了大半。如此大功,公父要視而不見麼?”
劉善德眼中一向沉着的眸中也燃起了熾熱的火,他一腳踹上劉圖南的心口。世子歪倒,撞翻了旁邊供案上的燈燭。
劉圖南摔在案上,望着斜倒的燈燭中的油垂落下來,連成一條細密的線,又轉成一滴滴的珠。他不懂,不懂為何如此簡單的道理,公父和杜相卻如此縮手縮腳。
“自古以來,邦國建交素來是以衆暴寡、倚強淩弱。弱國,無邦交。”
劉善德眼中的火熄了,變成了死一般的靜。他語調恢複了正常,說:“太平方出盛世,戰亂隻增徒勞。
劉緻,你愧對先祖、目無尊長、桀骜不馴,毫無公器之心。我看這世子,自今日起,不做也罷。”
劉主公将袖一拂,恨然離去,隻留下劉圖南癡癡地跌坐着,望着滿堂躍動的長命燭、和一地淩亂的供香。
次日正式文書下來的時候,比劉緻想象中更糟糕。
“……世子劉緻,背德敗行,目無尊上,不尊師訓,不從上命……巴蜀劉氏,世代以仁愛王道達濟益州,世子不為邦國興甯之思,不做勵精圖治之想,益州斷不可付與此人。即日起,褫奪虎符,奪‘雲臨君’封号,廢為庶人……”
☆、忠心
新城。
新野太守府。
蔔醒捧着面碗,将鞋履架在書案一角,一品着新野寬面的美味。他吃得噴香,樂得履尖翹頭不住顫動。
他聽到門外有響動,陡然收了放肆的鞋履,端正坐好,等着劉圖南推門而入,朗聲大笑誇贊他。
襄陽圍困戰過去了幾日,按照以往的慣例,劉圖南應該來探他了。陡然隔了這麼久沒見人,甚至連個信兒都沒有,反而讓蔔醒心中有些挂念起來。
來人的步子不如圖南世子般铿锵,反而帶着些沉靜的款款。
門吱呀拉開,來人寬袍深衣,三采黑绶,溫潤謙和。他見着醉靈捧着面碗,淺淺一樂,笑道:“醉靈都要官拜大将軍了,還是如此放浪不羁。”
蔔醒從木椅上緩緩站起,驚地面碗都忘了放下,他問:“仲廉莫要玩笑,益州素來丞相開府,不設大将軍。那都是吳國才有的官制。”
尚書令[1]吳仲廉幾步入了廳堂,笑道:“為你獨獨頭一例,那不是更加殊榮。”
他身後跟着以為低着頭的小屬官,恭恭敬敬地彎腰托着新制的紫绶金印。
“紫绶金印同主公手書一并帶來,益州虎符還需醉靈親自跑一趟益州,當面去領。”
吳仲廉說完,清了清嗓,醉靈放下面碗急忙上前跪着聽令。吳仲廉音色頗為好聽,一如朗朗清風。
手書念畢,蔔醒按着禮數恭敬行禮,這才接了绶帶印鑒。
吳仲廉合手行禮:“恭喜恭喜,蔔大将軍。”
蔔醒打哈哈道:“同喜同喜,仲廉尚書。”
他手中掂着沉沉的印鑒,給吳仲廉使了個眼色。吳仲廉當下會意,将随行來的小屬官遣退了。
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
相鄰推薦:我要那隻老虎的 五零炮灰的甜蜜生活 耕讀人家(科舉) 客官,火葬場有請(重生) 三國:封地1秒漲1兵,百萬鐵騎繞京城 [紅樓]二月是許願的時節 原來我沒有中二病 約會當天,末世就爆發了 巨星從搞笑開始 拯救校園的偏執少年[穿書] 離婚後我一夜爆紅[穿書] 七零之男配不做老實人[穿書] 重生大小姐野又飒,撩翻禁欲大佬 穿成騎士次子的我有個聊天群 反派暴君的早夭未婚妻 這個狐仙太不是人了 團寵小奶包,農家福妹竟是真千金 不良僞妻 不當舔狗,開局約會女神校花 魂穿之閻王看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