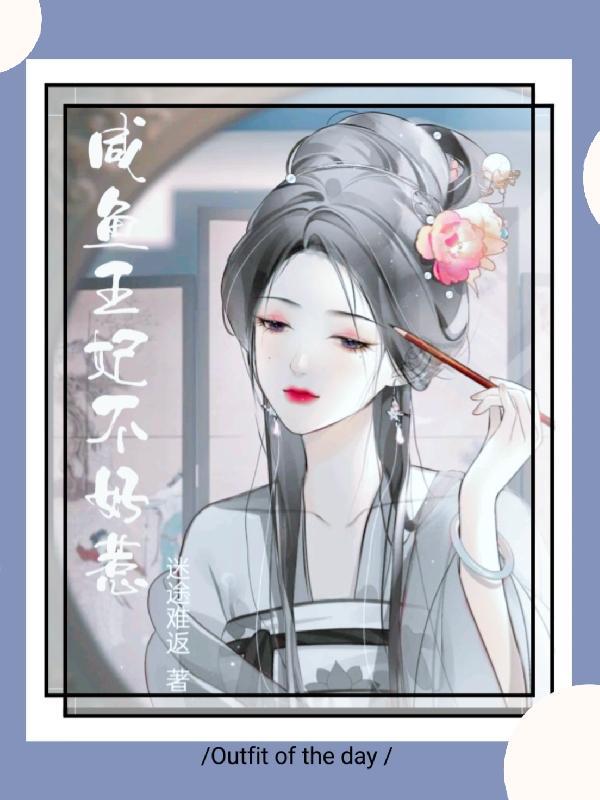書趣閣>紅風紅風 > 第22章 一個母親的傷悲(第1頁)
第22章 一個母親的傷悲(第1頁)
羅烈把要辦的事項轉告給老人。老人說,我不知道什麼辦,去哪裡辦,還請你們多幫忙。羅烈說,好吧我帶您去醫院辦理。我在屋外等您,您準備一下,千萬記得帶上您女兒的身份證、病曆,以及您的身份證。
羅烈說完走出門外等候。約五分鐘,羅烈和老人下樓。
門廳外的走道邊停着一輛兩輪電力巡邏車,是羅烈吩咐董滿山找來的。羅烈騎上巡邏車,搭着老人離開小區,向七公裡外成陽路的三立醫院駛去。
巡邏車穿行在燈火璀璨、車流如潮的道路上,羅烈不敢開得太快,他不時回頭提醒老人扶好坐好,生怕她有什麼閃失。
從704室的房門打開的那一瞬到現在,羅烈覺得背後的老人看起來并不像沉浸在悲傷的河流中。覺得她應該為女兒的死付出應有的幾滴堿淚——不奢求呼天搶地、痛哭流涕、暴風驟雨的模樣。最起碼有一點失态或者悲傷的神情,唯有如此才符合自然反應和人之常情,但這些并沒有在老人身上有所體現,她顯得太過于冷漠和平靜了。
為什麼呢?他們是母女關系嗎?她為何這樣?沒道理,講不通呀!然而又想,懷疑是不道德的,尤其在别人剛剛失去親人,最無助的節骨眼上。
可能悲傷埋藏在她的心底,不想讓人瞧見和分擔;或者她早已被困窘、麻木和無奈的生活所代替,沉默是她最好的裝飾,淚水也許早已枯竭,誰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女兒過去都經曆了什麼。
羅烈的思緒跟十字路口的車流一樣擁擠。不時偏離正在無限展開的夜路——喧鬧而紛亂——為老人感到難過——一種本能的難過——跟深沉還有一段距離的難過;同時也為女人深感惋惜,她看上去還年輕,不會超過四十歲。
他試圖回憶起剛死去的女人的容貌,出于一種莫名的難于形容的感傷。但記憶的儲存器完全失靈了,再也還原不出一張完整清晰的臉龐。
他再也想不起她的臉型、她的眼睛、她的眉毛、她的鼻子是怎樣的形狀?它們早已被某種神秘的力量删除,或者被呼嘯在耳畔的涼風擄去——腦海似乎隻剩下模糊閃現的——塗了三個紫色指甲油的一隻左手,以及可能是煙油熏染的永遠沉默的一口黑牙。
二十分鐘後,羅烈載着老人來到三立醫院。
羅烈和老人在醫院裡尋找和等待了一個多小時才見到之前宣告女人不治的男醫生,由他負責為死者出具死亡證明書。
會診室裡,消毒液刺鼻的味道在空中彌漫着,可以感覺到它們在瘋狂地剿殺可能到處遊蕩的某種看不見的病毒或細菌。
羅烈從醫生和老人的問答以及證明材料中得知:今天是女人三十八歲的生日,姓朱。她去年确診了宮頸癌晚期,一個月後離婚。不久她來到千裡之外的煙鼓市開了一間美容室,一邊工作一邊治病。她有個十一歲的兒子,跟他的父親生活。
出于好奇,他想知道她的前夫和兒子在她死前是否來看過她?可惜醫生沒問,老人也沒談起。他很想問,但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似乎有一個聲音在抗議:夠了,你的念頭是一把紮在别人心口上的毒刀,而不是一顆良善之心……
醫生寫好證明,就差簽字蓋章了,他交給老人幾張單據,叫她去收費處交費再來取證。
老人去了很久不見回來。
羅烈去收費處找人。看見老人坐在一張藍色的膠椅上,正在點數和捋着從手提袋裡翻出的一張張皺巴巴的小票和十幾枚硬币。她那雙枯瘦微顫的雙手不什麼聽使喚。
羅烈走近老人,很多硬币突然從老人的手上滑落,嘩啦叮當地撒在光滑的地闆上。它們到處蹦跶:有五毛兩毛的,有一毛一元的、有五分兩分的,有金黃色的,也有銀白色的……
收費室裡的五六個人被錢币摔疼的叫聲驚到了,紛紛向老人和錢币投去詫異的目光。
老人搖晃着從椅子上站起來去攆其中的一枚奔跑的硬币。
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
相鄰推薦:至尊龍婿陸凡 快穿之炮灰不走劇情 重生之驕娘不眼瞎 紅纓槍破杳杳雲 晝眠春信 病弱白月光一身反骨 [咒術回戰]飼養五條悟的那些年 深情男配的炮灰前妻佛系躺平了 重生大佬馬甲多,五個哥哥争着寵 萬人迷嬌寵手冊 滿級甜誘!被顧爺撩得夜夜腿軟! 穿替身後,她連夜攻讀月嫂手冊葉輕輕周越城 這個法師怎麼比戰士還能打 遊戲降臨之我是妖王收割機 十國藩鎮 被娛樂圈封殺,我蒙面做直播 年少無名 破産後,召喚皇帝們給我打工暴富 盜墓筆記:萬象重歸 萬俟之下